2025 年 3 月的某个雨夜,我盯着儿子小明作业本上鲜红的 62 分,笔尖在 “慰藉” 一词上晕开墨团。这个总在数学卷子上画满星星的孩子,此刻正咬着笔杆憋作文,半小时过去了,稿纸上还歪歪扭扭躺着五句话:”今天陪妈妈去巴刹,看到卖鱼的阿姨……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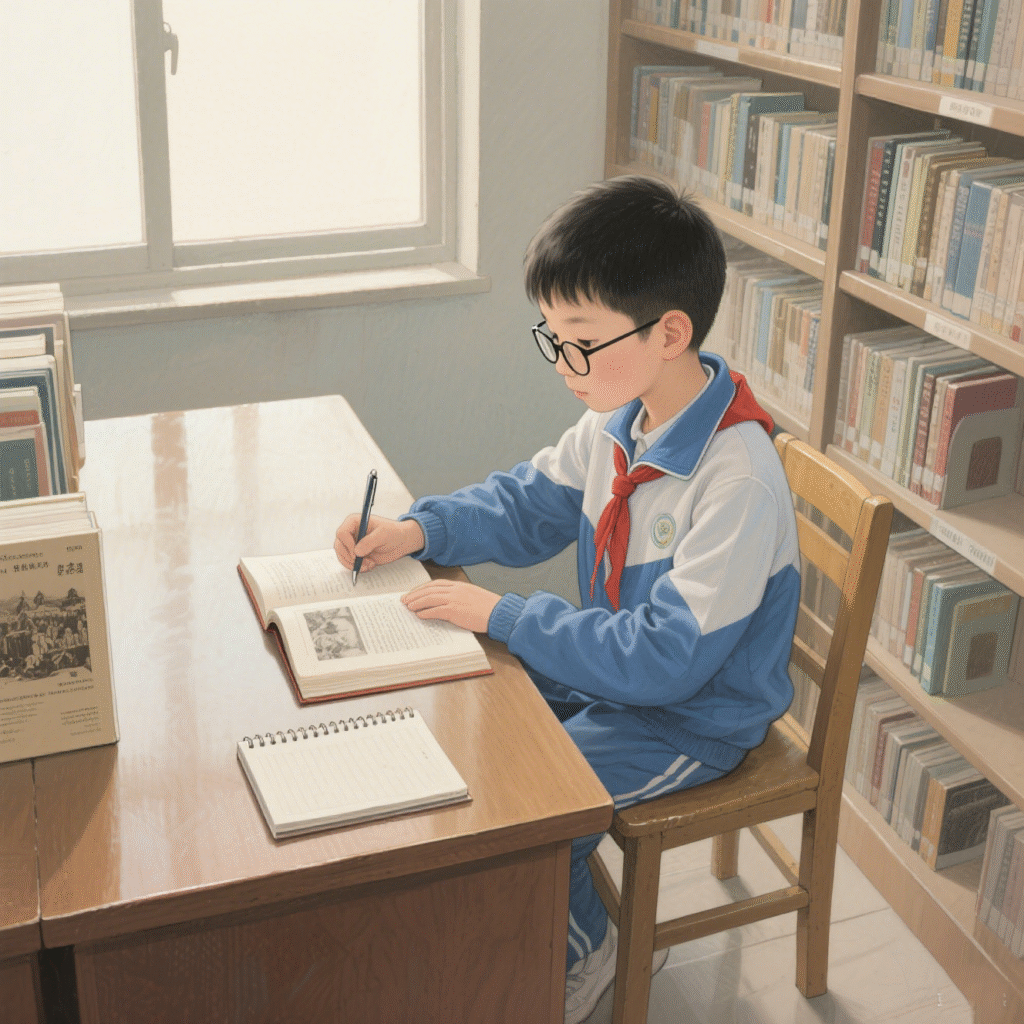
作为在新加坡长大的 ABC,我从小就对华文又爱又恨。爱它是母语,恨它总在关键时刻拖后腿。如今轮到儿子,问题更棘手了:拼音带着浓浓的 Singlish 口音,”祝福” 读成 “zhu fu”,”辜负” 永远少写一点;阅读理解像猜谜,常常对着 “作者表达了什么情感” 的题目抓耳挠腮;最要命的是作文,永远停留在 “流水账” 阶段,连学校华文老师都在联络簿上建议:”或许需要专业辅导。”
每个辅导作业的晚上都是一场战役。我对着谷歌翻译教文言文,他却把 “之乎者也” 和游戏里的 “必杀技” 搞混;报了线下大班课,每周三次往返金文泰,堵车时孩子在后排昏昏欲睡,到了教室早已没了学习劲头。三个月过去,成绩纹丝不动,反而多了句口头禅:”华文好难啊,我肯定学不好。”
转机是在红山小贩中心遇见林太太。她的女儿去年 PSLE 华文拿了 A*,正兴奋地给我们看手机里的作文奖状。”别信什么大班课,” 她戳着手机屏幕,”我给女儿找的线上 1 对 1,老师连她爱用 ‘ 然后 ‘ 开头的毛病都治好了。”
当天下午,我就给小明约了 Sino-bus的试听课。ClassIn 课堂打开的瞬间,孩子的眼睛亮了 —— 老师用动画演示 “山” 字的演变,从甲骨文的三峰并列到楷书的竖折竖,配合着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的照片,”原来汉字是画出来的!” 小明跟着老师在互动白板上描摹,第一次主动开口念拼音。
张老师的诊断精准得像 CT 扫描:拼音混淆是双语环境下的常见问题,作文薄弱源于缺乏贴近生活的素材。第一节课后,我收到详细的学习报告,连孩子握笔姿势影响书写速度都被记录在案。更让我惊喜的是,老师布置的作业居然是观察湿巴刹:”明天和妈妈去买鱼时,注意阿姨称鱼的动作,阿婆包粽子时粽叶怎么折,这些细节都能写成作文。”
从此,每天傍晚六点成了小明最期待的时光。打开电脑,张老师总会变着法儿让华文课充满惊喜:教 “b/p” 发音时,用滨海湾金沙酒店的 “船帆” 比喻 “b” 的挺拔,用鱼尾狮喷水的 “弧度” 讲解 “p” 的爆破音;解析古诗《静夜思》,对比新加坡的月圆庆典,”原来李白和我们一样,看到月亮会想家。”
课后服务同样贴心。专属学习群里,老师随时解答作业疑问,连我这个妈妈都跟着学会了 “如何区分 ‘ 的地得 ‘”;课堂录像可以无限回放,小明常指着屏幕说:”妈妈你看,这里老师用组屋晾衣绳讲 ‘ 亡羊补牢 ‘,现在我再也不会用错成语了。”
上个月,小明参加学校的华文故事创作赛,用《汉字里的新加坡》拿下银奖。领奖时他说:”原来华文不是难学的科目,而是打开我们文化的钥匙。” 看着台上自信的孩子,我突然想起试听课那天,张老师说的那句话:”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学习节奏,我们要做的,就是找到那把合适的钥匙。”
如今的晚上七点,不再有作业大战。小明会主动打开 ClassIn,复习课堂录像里的拼音游戏;遇到不会写的字,不再喊 “妈妈救命”,而是说:”等我问问张老师有没有更有趣的记法。” 这场华文逆袭之旅让我明白:最好的教育,不是填鸭式的灌输,而是找到孩子的痛点,用耐心和专业搭建桥梁。
如果说有什么遗憾,那就是没早点遇见 Sino-bus。但正如林太太说的:”教育永远不怕晚,只要找对方法。” 现在的我们,正期待着下一次进步 —— 不是因为分数,而是因为孩子眼中重新燃起的对华文的热爱。这,才是最珍贵的收获。
Contact us WhatsApp:+8618165329059
